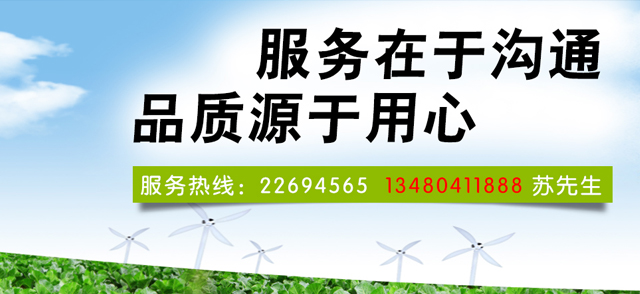幾千年來,古人“胡”“番”“洋”給這些外來蔬果輪番起名
辣椒直到明末才傳入中國,民間普遍開始吃辣椒更是在清道光以后。因此,段譽那個年代的人怕是根本不知辣椒為何物。
辣椒。攝影/三溪攝影,來源/圖蟲創意
當然,小細節并不影響金庸著作的精彩程度。但由此卻引發了一個讓人非常好奇的新問題:餐桌上我們吃慣了的蔬菜,哪些是土生土長的,哪些是“外來戶”呢?
要想區分它們其實并不困難,名字上就有跡可循。著名農史學家石聲漢曾根據引進瓜果蔬菜的命名規律,劃分出了“胡”“番”“洋”等各大“家族”。
“胡”:早期大戶
兩漢、兩晉直至隋唐,從陸路引入的作物種類,多數用“胡”字標明。
春秋戰國時代,中原諸侯并稱諸夏與中國,以與周邊各族對舉,非我族類的“胡”,這時便已出現。兩漢時期,“胡”常指匈奴,后又被引申為“古代北方和西方的其他少數民族”——到西晉末年的“五胡”,就分指匈奴、鮮卑、羯、羌、氐這幾個大部落。而《集韻》(多以東漢《說文解字》為根據)一書中也明確指出:“胡,虜總稱”。
隋唐時期,由于對外貿易迅猛發展,“胡”進一步引申為西域諸國(包括天竺、波斯、大秦等),來自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商人統稱為“胡商”,而由他們帶來的東西,也都會被冠上一個“胡”字。比如白居易在詩中曾提到風靡中原的西域面食“胡餅”:“胡麻餅樣學京都,面脆油香新出爐。寄與饑饞楊大使,嘗看得似輔興無。”
從秦漢到隋唐,這樣的命名傳統,也在外來瓜果蔬菜上得到延續。
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,開辟了從長安經今寧夏、甘肅、新疆到達中亞細亞內陸的絲綢之路,開啟了中西方農業科技文化交流的第一段繁榮時期。張騫及其使團返回漢朝時,帶來了大量的外來物種。
張騫出使西域。來源/紀錄片《中國通史》截圖
《博物志》曰:“張騫使西域, 得大蒜、胡荽。”
其中的“大蒜”,最初被稱為“胡蒜”,源于大宛國。當時,我國本來就產蒜,和胡蒜相比只有大小的區別,因此,后來就以大小蒜分別稱呼。李時珍在《本草綱目》卷二十六“蒜”中就指出:“中國初惟有此(小蒜),后因漢人得胡蒜于西域,遂呼此為小蒜以別之。” 東漢時期,大蒜的傳播已經遍及全國,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的美蔬佳料。
“胡荽”就是我們現在說的芫荽,即香菜、香荽。香菜是人類種植歷史上最為古老的芳香蔬菜之一,原產于地中海沿岸即中亞地區,據說考古學家曾在古埃及法老圖坦卡蒙的墓穴中發現香菜的種子。
香菜。攝影/vaivirga,來源/圖蟲創意
關于它傳入中國的時間一直都有爭議,許多學者對《博物志》的說法持保留態度,認為芫荽出現在我國的時期要晚于張騫出使西域。至晚到了南北朝時期,這個有著奇特味道的蔬菜已經受到中國食客的普遍認可。成書于北魏末年的農學著作《齊民要術》,就詳細論述了種植芫荽所需的各種自然條件,并且比較了不同地區、不同方法種植出來的芫荽在品質上有何差異。
不過,要說起“胡”字開頭的蔬菜,“胡蘿卜”肯定不能錯過。比起前面提到的兩位前輩,胡蘿卜進入中國的時間較晚,比較常見的一種說法是在元代傳入。主要依據是李時珍的《本草綱目》,書中云:“元時始自胡地來,氣味微似蘿卜,故名。”
但這種說法也遭到質疑,有人認為胡蘿卜至晚在宋代就已傳入中國。南宋高宗紹興年間,王繼先等人奉旨修成《紹興本草》,其中就出現過胡蘿卜;南宋傳奇廚娘浦江吳氏也在自己的食譜中記錄過“胡蘿卜鲊”一菜:“(胡蘿卜)切作片子,滾湯略灼,控干。入少許蔥花、大小茴香、姜、橘絲、花椒末、紅曲,研爛,同鹽拌勻,罨一時食之。”
電視劇人物吃胡蘿卜。來源/電視劇《歡喜密探》截圖
還有一個我們耳熟能詳的蔬菜,也出自“胡”姓家族,那就是黃瓜。和大蒜一樣,黃瓜也在漢時從西域傳入,同樣也有個原名,叫“胡瓜”。
《齊民要術》中寫道:“收胡瓜,候色黃則摘。”成熟之后皮會變成黃色,也就是我們今天稱為“黃瓜”的原因。但它最早之所以改名,并不只是因為這一個簡單的理由。
究其原因,普遍的說法是后趙開國皇帝石勒因為自己是羯族,所以諱稱“胡”字,就把胡瓜、胡蒜等作物的名字都給改了。不過,史學界也有不同的聲音,認為隋煬帝改名之說更為可信。
根據唐代吳兢的《貞觀政要》:“隋煬帝性好猜防,專信邪道,大忌胡人,乃至謂胡床為交床,胡瓜為黃瓜,筑長城以避胡。”到了北宋蘇軾的《浣溪沙》中,胡瓜就已經被“改造”成黃瓜:“簌簌衣巾落棗花,村南村北響繰車。牛衣古柳賣黃瓜。”
值得一提的是,在明清時期,黃瓜還多出個霸氣外露的別稱——“王瓜”。這個名字之所以流行開來,很可能是因為“王”“黃”二字發音相近,而“王”筆畫更簡單。
黃瓜。攝影/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сенко,來源/圖蟲創意
明代小說《金瓶梅》曾寫過不少酒席菜肴,其中的“案鮮”就包括一道“曲灣灣的王瓜拌遼東金蝦”;明代王世懋的《學圃余疏》則記錄了“溫室黃瓜”的栽培過程:“王瓜出燕京最佳,其地人種之火室中,逼生花葉……”;而作為反季節蔬菜的代表,黃瓜的昂貴程度在清代這首《京都竹枝詞》中展現得淋漓盡致:“黃瓜初見比人參,小小如簪值數金。微物不能增壽命,萬錢一食亦何心?”
除了上述例子,今天的豌豆、芝麻、核桃等等,在過去都有個“胡”名,分別叫“胡豆”“胡麻”(非今天的胡麻)“胡桃”。從“胡姓作物”數量之龐大,足以窺見當時的中國對外交往有多么活躍。
番:明朝望族
宋元至明清時期,從域外傳入的作物多冠以“番”字,表示是由“番舶(外國海船)”帶來的。這種稱呼,也與古代中國的文化認知有關。
帶“番”的名字,往往從閩粵地區流傳開來。根據閩粵地區的方言,外國人被稱為“番人”或“番鬼”——直到今天,香港市井仍然有人稱啤酒為番鬼老涼茶,中國臺灣地區民眾也會稱火柴為“番仔火”。
隨著世界航海大發現,原產于美洲大陸的許多瓜果蔬菜都在明代遠渡重洋來到中國。今天的番薯、番茄、南瓜、辣椒等等,都是這一時期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傳入的。
番茄,也稱番柿,原產于南美洲安第斯山地帶。在我國最早的記載,見于明萬歷四十一年(1613)山西的《猗氏縣志》,在其中被稱為“西番柿”,由歐洲傳教士引入;而后王象晉所著的《群芳譜》中出現了更加細致的闡述:“番柿,一名六月柿,莖如蒿,高四五尺,葉似艾,花似榴,一枝結五實或三四實,一樹二三十實,……來自西番,故名。”
【免責聲明:本網站內容,有來自于網絡文章,并不代表本站觀點、立場,本站也不為其真實性負責,只為傳播網絡信息為目的,如文章有侵權請及時聯系,將予以刪除】